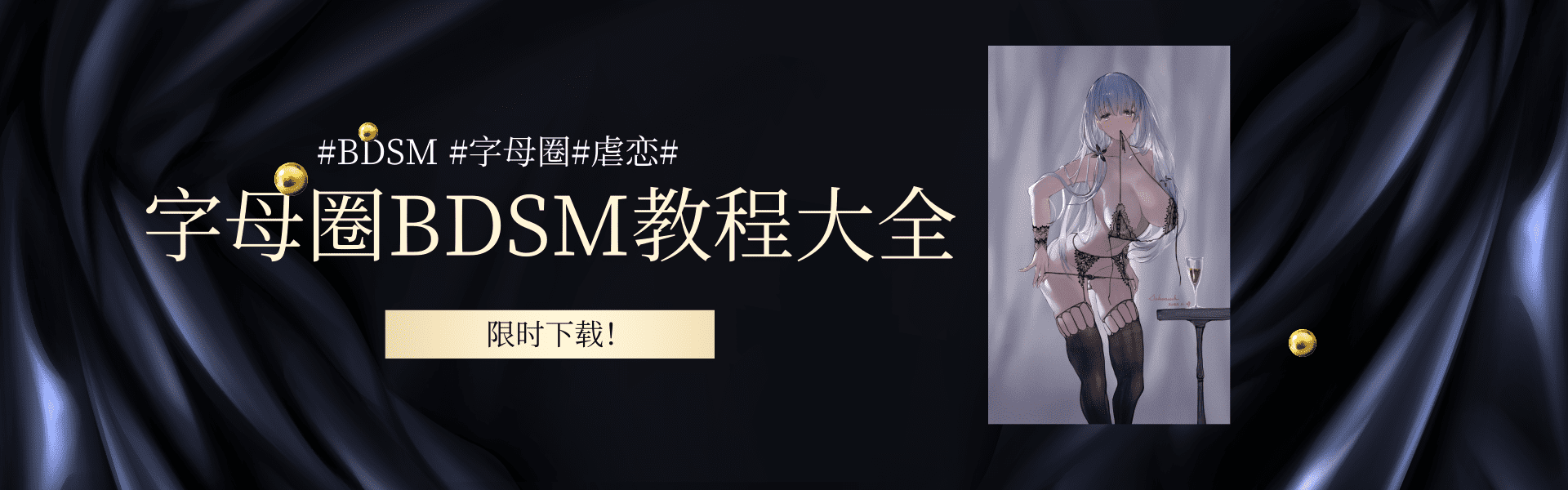我的鞭子很爱你
一个叫E·L·詹姆斯的女人写了一本叫做《五十度灰》的小说,迅速成了全球畅销书。根据这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情人节”首映,别有意味。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却是在虐中施爱。也许因为作者是家庭妇女,身份局限,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女主人公终究“政治正确”地不接受“虐恋”。我倒欣赏60年前的《O的故事》的作者,也是女性,虽然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用了一个“波利娜·雷阿热”的笔名,但她却让她的女主人公O最终爱上了施虐者斯蒂芬,离开他宁可死。
女性自叙,勿宁给男权主义者提供了口实。法兰西学院院士鲍尔汉在《O的故事》序言里兴奋地叫道:“终于有一个女人承认了!这就是男人们对她们一向所持的看法:她们从来不会不遵从他们的本性,她们的血液中带来的召唤,这一包容一切的甚至将她们的灵魂包括在内的召唤,就是性。她们不断地被养护、被洗涤、被装饰,不断地被鞭打……简言之,当我们去看她们时,我们必须带上鞭子。”鲍尔汉几乎重复了尼采的话。而女权主义者则对这部作品咬牙切齿,痛恨这个性别同类向男权体制缴械投降。
什么是男权体制?凯特·米莉特在《性政治》中做了详细描述。“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甚至那超自然的权力——神权,或‘上帝’的权力,连同它有关部门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或者,就像T·S·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创造的。”这种创造,让男人“将自己树立为人的典范,在他这一主体或对象的对立面是一个‘异己的’或敌对的女人。”于是,当尼采说出“要去见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时,虽然我们会感觉极端,但是潜意识里还是认同这种暴力。“虐恋”就是建立在这种暴力逻辑上的契约。当然,这是男人单方的契约。
施虐常常以鞭打作为形式,作为刑具的鞭子本身就具有象征性。霭理士认为:“鞭棍一类的名词往往也就是阳具的称号”,弗洛伊德也说:“人们都熟知马鞭、手杖、长矛以及类似物都是阳具的象征;但是马鞭更具有阳具的最显著的一个特证,即其延展性,其象征意义就更确凿无疑了。”在汉语中,“鞭”也具有雄性生殖器的义项,诸如“鹿鞭”、“虎鞭”之类。男人用鞭棍打女人,彰显其至高无上的权力。鞭笞时对方往往需要俯身,这是灵长类动物可耻的姿势,表示的是臣服。所以古代以鞭杖刑法来彰显体制的权威。《明律译义》曰:“笞者,耻也,乃使人受辱,是为惩戒而设。”
这只是显性暴力。很多人只把“虐恋”理解成一种显性行为,这是浅薄与狭隘。“虐恋”本质上是精神“虐恋”。这点在基督宗教上就相当明显。从政治学上观察,这种精神上的施受虐就是体制的统治和被统治。按汉纳·阿伦特的看法,统治由两种权力维系,第一种权力来自公众对该权力的认同,第二种权力是通过暴力强加的。如果统治形式努力通过自我调节以符合某一意识形态,它就属前一类。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男人往往害怕变成女人,这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贬低和羞辱。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着把男人变成女人进行羞辱的故事。割除男性生殖器被称为“阉割”,其贬低的含义十分明显。中国还称为“去势”,那么男性生殖器“进入”女性身体,即是其“势”的胜利,于是也就顺理成章有了“征服”、“占有”、“御幸”的感觉。我的小说《大势》写的就是男人对“势”的焦虑,每次“进入”女性,对他来说都是对自己权力的检阅,所以他竭尽凶暴。几乎所有男性对女性的性行为,都充满了暴力的想象。
暴力必须得到证明,性对象的女性的痛苦表情乃至“叫春”即是证明。所谓“叫春”,实际上是叫出“男人之春”。而让处女膜破裂,更是“首暴”的证明,从此这个女人归属于我。许多“虐恋”作品中有这样的细节:男性施虐者在女性受虐者身体上打上自己的印记。波利娜·雷阿热《O的故事》里,施虐者斯蒂芬在O的身上打上了他姓名的烙印,让O成为自己的属物,《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做法跟斯蒂芬惊人的相似,他也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留下烧疤,谓为“烧柱香儿”、“烧情疤”。在女人身上“烧情疤”,和马的主人用烧红的铁块在马屁股上烙上印记类似。男人把女人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以“疤”为证。最深也就最牢靠的“疤”是“进入”身体后留下的,那是永不可磨灭的。女人也因为被戳上这个印迹,觉得自己是对方的人了,或者自惭形秽。
男人的权力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以及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客观性中,也体现在所有的观念的固有模式中。布尔迪厄说:“由于这些模式受到类似条件的作用,所以在客观上被接受,作为社会所有成员的认识、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发挥作用。”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接受了这种模式,她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她所遭受的象征暴力。”“象征”即是能被那些懂得规约的人所理解的规约,就好像军服上的军衔条纹。女人读懂了它,认可了它,服从了它,她们自惭形秽,自我贬低。
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学叙事中,哪怕是开明的写作者,甚至声称为妇女解放,都难以逃脱其窠臼。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里声援小芹的婚姻解放,但对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却冷嘲热讽。三仙姑有什么值得讽刺的呢?老之将至,却还喜欢打扮,“老来俏”。区长指责她:“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为什么老女人打扮就不像个人?三仙姑也屈从了:“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走什么俏?”
女人如果不屈服,那就成了悍妇。莎士比亚《驯悍记》里就有这么一个悍妇。凯瑟琳娜秉性暴躁,悍声远播,以至于求婚者都不敢问津。莎士比亚设置了维洛那绅士彼特鲁乔对她进行驯戒。其实她的凶悍不无道理,她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婚姻上不受别人支配。但是因为她是女人,她的诉求是不符合体制规约的,她最终也服从了规约。
有意思的是,彼特鲁乔驯戒凯瑟琳娜,理由是“为了你好”。“虐恋”中的施虐方往往是以“为了你好”的理由实行施虐的,英国诗人斯宾文《鞭笞台》就表现了教育与施虐的“同构”关系,日本“虐恋”小说或电影里把对女人的施虐称为“调教”。教育的理由使得施虐具有正当性。《金瓶梅》里西门庆鞭打潘金莲也有理由:我不在家,你偷人。男人西门庆可以寻花问柳,女人潘金莲则不能偷人。而潘金莲也“自知理亏”。如果说西门庆被描绘成反面形象,不具有正当性,武松是被描绘成正面形象的,但他的逻辑与西门庆并无区别。在武松面前,潘金莲是个荡妇,必须被虐杀。
“有压迫就有反抗。”男人对女人施虐,女人也对男人施虐。让(娜)·德·贝格就在她的《女人的盛典》里幻想女主人公对男人施虐。“我曾经渴望着用蛋来弄脏一个男人。这是我很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有的念头。”“您看过那部叫做《欲念浮动》的影片吗?其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个年轻女人把一些蛋打在另一个女儿身上。那些蛋被轻巧地放下,因此尽管它们移动着,它们颤微微的,但他们并没有散裂开来。我曾经渴望着另一回事。我曾经渴望着,恰恰相反,它们散裂开来。我一直希望用活话的形式重组‘圣·塞巴斯蒂安受虐’一画,在上面箭将由蛋替代。这场演出需要一种特殊的布景(一堵光秃秃的墙,一块经得起任何状况的地面)以及一个出色的‘男演员’。我在同一个星期内碰到了一个和另一个:一个漂亮的奴隶,我觉得他应该扮演一个理想的圣·塞巴斯蒂安;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一间空房间其中整整一堵墙上面镶着镜子,还有一块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地面。”
男人对女人施虐,随时随地发生在现实生活场景中,女人对男人施虐,更多时候只能经过刻意的安排。《女人的盛典》的女主人公进入的是一个“虐恋俱乐部”,但这里的设施、场景跟《O的故事》如出一辙。就连情节也很类似,不过是置换了性别。蒙眼,脱衣。“我给他脱下衣服,一点一点地(有点粗暴,我必须承认,因为我撕破了他的T恤),我们同时还评头论足。”弄污,捆绑,下跪,羞辱,当然还有鞭打。不仅女主人公自己鞭打男人,还让她的女仆鞭打。跟《O的故事》一样,《女人的盛典》最后也发展到了“进入”。不过这下不是男人对女人,而是女人对男人,虽然“进入”的不是女主人公自己,她让女仆代为行事。但是,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客观上构造迥异,那是谁“进入”谁呢?罗曼·波兰斯基的《死亡与少女》中,那个被男人强奸的女人激愤时曾想过“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身”,也去强奸那个男人。但是她马上意识到了,这勿宁又沦为被男人强奸。
“虐恋”译自英语sadomasochism,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来源于作家萨德的sadism,一是来源于作家莫索克的masochism。前者是施虐,后者是受虐。无论是男人施虐女人受虐,还是女人施虐男人受虐,都还不能充分展现虐恋的诡异图景。作为作家的莫索克的特殊性在于,他揭示了男人的受虐欲望。他的《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的萨乌宁渴望成为“女王”旺达的奴隶:
我走了进去。她坐在屋子中间,穿着白色绸缎做的袍子,袍子很贴身,就像光一样从她身体直泻而下。她还穿着一件奢华的装饰了貂皮的、鲜红色绸缎做的外套。扑了粉的头发上戴着镶宝石的花冠,胳膊交叉,放在胸前,眉头紧蹙。
“旺达!”我急忙跑向她,试着拥抱她,亲吻她。她后退了一步,从头到脚仔细地观察着我。
“奴隶!”
“主人!”我跪下来,亲吻她袍子的花边。
“这正是我所要的。”
“哦,多么漂亮啊!”
“你喜欢我吗?”她走到镜子面前,自豪地端详着自己。
“我都快要得精神病啦!”
她的下嘴唇讽刺地抽动了一下,半闭的眼睛嘲讽地看了我一眼。
“给我鞭子。”
我环顾四周。
“不,”他嚷道,“你一直跪着!”她踱到壁炉前,从壁炉架上取下鞭子,冲我傻笑,抖动着鞭子,鞭子在空气中忽忽作响。然后,她慢慢卷起毛皮夹子袖子。
“多么奇妙的女人!”我嚷道。
“安静,奴隶!”她突然瞪了我一眼,相当野蛮。鞭子抽中了我。但是,下一秒钟她就温柔地绕着我的脖子,同情地靠近我。“我伤着你了吗?”她问道,半是尴尬,半是焦急。
“没有。”我否认道,“你这样做,折磨我,弄痛我也觉得是一种快乐。只要你喜欢,就接着鞭打我吧。”
他要给她立“奴隶契约”。这下是女人虐待男人的契约。
无独有偶,在东方的日本也有这样一个男人,他是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里的主人公佐助。佐助自愿跟随女主人春琴,接受她的虐待。他本来可以回到自己家中继承家业的,但是他拒绝了。当春琴被人毁容,不愿让他看到丑陋的面容,他决然把自己的眼睛刺瞎。谷崎润一郎许多作品都有虐恋内容,他早期的《饶太郎》就写了男主人公迷恋于被女人拷打。在他的《痴人之爱》里,男主人公河合让治被一个混血女子娜奥密搞得神魂颠倒,自甘受虐,“跪在她脚下”。这种男性自愿受虐叙事在川端康成、水上勉等作家的笔下也不少见。日本男作家喜欢讲述女虐男的故事,女人高高在上,男人匍伏在地,男人把女人当做“女王”。岂止作家,日本男人普遍有着“跪在她脚下”的情结。这竟然发生在男权意识强烈的日本,似乎令人不解。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勿宁是男权的一种变种。
实际上,统治与被统治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男人统治了女人,勿宁是掉进了陷阱,结果是正如布尔迪厄所分析的:“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一方面,统治者从统治中受益,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将无意识的模式用于自身”,这使得他们不堪重负。
心理学家瑞奇指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性格盔甲”的东西,它像盔甲一样包裹着人的全身心,让压力无法排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形成焦虑和恐惧之时,他就急待来自外力的打击,就好像一只胀满的汽球需要从外面扎一个孔,从而得以泄气。他得出人的快感模式:紧张——聚积——宣泄——放松,而受虐,就能达到宣泄和放松。
与《女人的盛典》一样,女人作为弱者,难以在现实中向男人施虐,选择了虐恋俱乐部;男人无法卸下盔甲,也走进了虐恋俱乐部。在这地方,女人和男人各取所需,女人成了“女王”,男人寻求“女王”鞭打自己。有资料表明,在美国的虐恋团体里,女性约占三分之一,这些女性绝大多数是施虐者,而男性绝大多数是希望扮演被虐的角色。而且,光顾这种地方的男人,往往在日常世界里身居高位,他们是总裁,是高管,是律师,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把盔甲脱掉,把权力放弃,接受“女王”的施虐。
但这只是男人暂时放弃权力,一旦不想放弃了,他又可以收回,他又是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快又会从奴仆变成了主人。明白地说,“女王”只是男人利用的工具,她们的恶只是男人创造的。正如三岛由纪夫谈谷崎润一郎时所说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看到,那不是女人生来具有的特别的罪恶,而是男人期待的一种罪恶,它反映了男性的欲望。”
我不知道《女人的圣典》里的女人,“一直希望用活话的形式重组‘圣·塞巴斯蒂安受虐’一画”,她是否意识到,让圣·塞巴斯蒂安受虐的愿望仍然被男人所利用,圣·塞巴斯蒂安在瓦拉奥画笔下变化成了《被圣妇照料的圣·塞马斯蒂安》。我发现,17世纪以来,艺术家们表现男性受虐的最常见方式,就是让受虐的英雄或圣徒被女人救助,同样的例子还有皮埃特的《坦克雷德被厄米尼亚所救》。救助者都是圣洁美丽的女性,同时,被救助者身上都被箭或者剑击中,他们在痛苦中颤抖着性的快感。
但是,女人是否真的被利用?当女人受虐时,是否就真的不能产生快感?那个法兰西学院的鲍尔汉院士是否道出了某些秘密?
弗洛伊德直言,女性的受虐倾向是“女性的本质”。他将受虐倾向归纳为三种类型:性欲基因型、道德型和女性气质型。他认为,受虐倾向对女性来说是常见的、正面的倾向,是性成熟的表现。受虐倾向是真正的女性气质。他的信徒、维也纳心理学家迪兹克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而女性具有希望被强奸和被侵犯的隐秘冲动。她认为女人的受虐倾向是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心理后果,拥有女性气质就要拥有受虐倾向。她宣称这一论点是被她的心理门诊临床经验所证实了的。她甚至说:受虐倾向是一个女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力量所在。
还有许多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也坚定地相信女性具有受虐倾向。玛丽亚·帕娜帕黛认为:女性的生殖器是被动的、接纳的,有着“被虐”的意涵。在性交过程中,女人其实是在接受男性性器的抽打,她默默忍受他的抽打,甚至是乐于接受他的暴力。而女性的生殖细胞也像她的性器一样被“穿刺”,受精实际上就是由精子钻入,由卵子在某种程度上受损,这个过程证明了女性的卵子也具有原始的受虐性。
要命的是她们是女性。这简直是“窝里反”。这确实是女性自我的“招供”,一如波利娜·雷阿热,是女人的自行羞辱。她们呼应了萨德:“我告诉过你,进到女人心里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折磨她。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事了。”
萨德这个名字长期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直到人类不得不正视自身。萨德近100年来才越来越被谈论,跟人类身陷自身困境有关。但是中国人乃至中国学界习惯于遮蔽。本世纪初我考博,面试的题目是谈一个西方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我谈了萨德,现场老师都对萨德不甚了了。当然严格上说,萨德对中国文学也影响甚少。至今人们还将之视为色情作家,这是对他的误读和贬低。看看罗兰·巴特怎么说萨德的:“萨德和傅立叶及罗耀拉一样,他们都不约而同创造了自己的语言系统。”
我一直觉得,这个系统并非来源于古希腊传统。相反,中国文学传统虽然绵延在遥远的东方,却跟古希腊传统在价值取向上基本吻合。那就是所谓的向往文明普世价值吧?几千年来,这个价值观浩浩荡荡,殊途同归。但萨德却是另一条河流。这恰恰是文学的河流。我说过,文学价值观并非俗世价值观,它是反俗世价值观。但似乎认可者少。当我读萨德,在广袤的文学场上,我感到形单影支。我常苦恼无法让人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也不明白他们隔靴搔痒意义所在,因为我受过了萨德之虐。萨德之虐绝不是简单的侵犯,不是浅薄的冒渎。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说:“萨德既用感性的事物羞辱了理性,又用倒错的理性羞辱了‘具有理性的’感性事物。”“由于行为倒错者的话语想成为常识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不离开规范化理性的概念范畴,该话语仍然停留在诡辩的范畴之内。只有当对话者也不得不抛弃规范时,才能够信服。萨德的人物不是通过理由来让对话者信服自己的,而是通过共谋。”
“共谋”,这是萨德抽向人类最致命鞭子,所以萨德必须一次次被投入监狱。
我总认为,日本文学乃至文艺是得“虐恋”真传的。典型的是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这是一个虐恋叙事,但没有城堡,没有刑具,女主人和男仆人也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主仆,作者设置的全是日常场景,讲述的是我们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爱情故事。但是这个爱却是在施虐者与被施虐者“共谋”下完成的。它没有猎奇,你无法将之视为传奇,也无法妖魔化它。它就是生活本身,就像卡夫卡以写实的笔触描绘出真实的场景,我们都被指涉到了,我们无法推诿,无所逃遁。它并非游戏,它撕开人类假惺惺的睡衣。这就是日本文学往往不能让人接受的原因。说日本文学情色,其实这世界上有的是情色,并且没人不喜欢,情色还可以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洗污成“崇尚自然”这个正价值;说日本文学暴力,暴力叙事并非完全不能被接受,比如“红色文学”,无论是革命战士杀敌,还是革命者受刑,都甚是暴力。即便是施刑,日本也只是绳缚。
绳缚可谓日本特色。西方“虐恋”道具多用鞭子,像艾兴格尔《被缚者》这样的小说毕竟少数。日本则多用绳。有人研究,绳这个创意来源于和服的绸带,众所周知和服来源于中国唐服,可惜的是,中华民族思维平庸,没能抵达极端的境界。中国虽然也有鞭子叙事,但也没有抵达西方的思辩性。西方的鞭子来源于马,马与人的关系是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但绳则不同,绳是柔软的,绳缚是暧昧的服从和被服从。鞭是外在之“虐恋”,绳是内在之“虐恋”,绳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处境的更深层的理解。按学者鹿岛茂的说法,绳缚象征着对自由的束缚。西方人崇尚自由,因而诞生了痛苦,必须张扬痛苦,从而接近神,得到救赎;而日本人心中并不存在唯一的神,要消除痛苦只能放弃自由。在绳缚中,绷紧之绳与起伏身体完美配合,自由和桎捁激情交流。
我们都在绳缚的痛苦和快感中,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我们都是体制的“共谋者”,包括我,一个写作的人,讲故事的人。人类讲故事起源于抵御生命的衰败和死亡,断死续生,这是西方自荷马以来的叙事传统,《十日谈》如此,其实《一千零一夜》也是如此,其实,中国的《聊斋志异》何尝不是如此?但萨德并不如此。他的《索多玛120天》也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但这些故事被死亡所缠祟,催动萨德讲这些故事的意志不是欲,而是死。但死亡也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欲,一种欢欣,死亡是终极的救赎。请想象一下一个常年被囚禁者与体制“共谋”的图景,这才是文学的图景。
来自于 布道字母 圈 www.bdsmbd.com